

北島有一首詩里說:
「我和這個世界不熟。這并非是我絕望的原因。我依舊有很多熱情,給分開,給死亡,給昨天,給安寂。」
這話就是加繆的真實寫照,他認為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然而他的生活,規規矩矩,得諾貝爾獎時就規規矩矩領獎,并不像薩特那樣直接拒絕。
他做記者時,采訪別人,報道世界,他做作家,描繪生活,探索人生的真實,他還以哲學家的銳利的眼光看到了生活的本質是荒誕,他同時拿著工資、拿著稿費、拿著各種獎項,他也買房,要不是一場交通事故,他會和任何一個正常人一樣,努力生活。
可在他的作品里,無時無刻不透著荒誕,《局外人》如此,《鼠疫》也如此,但對于荒誕,加繆的態度不是無作為,而是反抗,《局外人》里的默爾索在反抗,《鼠疫》里面的醫生也在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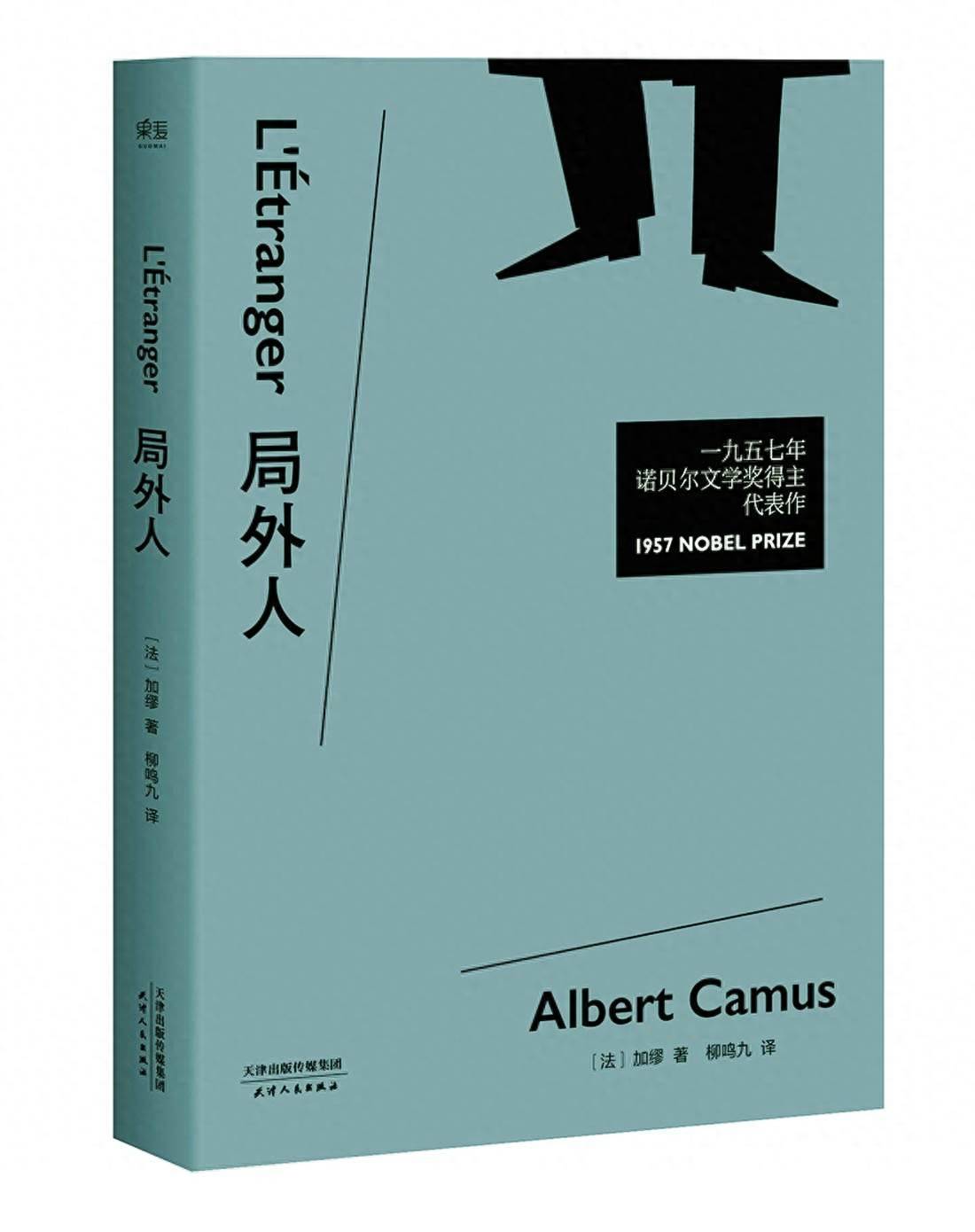
和《鼠疫》比起來,《局外人》缺少反抗,渺小的人在整個社會面前,虛弱無力,被無情碾碎,而命運對此,從無憐憫,過去已經發生的,明天還會發生。
盡管如此,這個荒誕的世界依舊不妨礙大多數人追求人生的幸福,追求生活的意義。

《局外人》的故事很簡單,三十多歲的默爾索,依舊是高齡未婚,過著躺平的生活,既不努力求上進,也不積極求改變,只是覺得,生活可以過下去就行,反正不管怎麼樣,最終都會習慣。
默爾索雖然躺平了,但世界還在加速運轉,養老院的母親突然去世,默爾索不得不回去。
他的母親是在養老院去世的,葬禮也在養老院舉行,令人詫異的是,他不知道母親的具體年紀,殯儀館的人要用釘子釘住棺材,問他要不要再見母親最后一眼,他也不見。
葬禮上,一些人神情悲哀,面無表情,還有人為母親落淚,可是作為兒子的默爾索,沒有哭,也沒有覺得痛苦,他只是百無聊賴地觀察別人,覺得一切都那麼快速,合乎常規。
葬禮結束后的第二天,默爾索和女友在游泳館嬉戲,兩人一起看了喜劇電影,晚上一起尋歡作樂。
你是不是覺得默爾索冷漠無情?是不是也覺得他對母親沒有愛?否則為什麼不哭,為什麼沒有痛苦,為什麼連母親的歲數都不知道?
默爾索身邊的人,就是這麼覺得的。
但默爾索并不覺得自己的做法有什麼不好,在他的生命里,似乎一切事情都是正常的,反正人總是要死的,生活總是要過下去的。
他說他愛母親,和其他人愛他們的母親一樣愛自己的母親。
他還是像以前一樣生活,混混鄰居雷蒙想結識他,請他幫忙,他也不拒絕,因為他覺得,既然認識也行,不認識也行,一切毫無意義,那就沒必要讓鄰居不滿意。
他幫雷蒙寫羞辱別人的信,在警察局幫雷蒙做假證,因為他覺得,做也行,不做也可以,一切皆無意義,那就沒必要讓別人不快。
這就是他的生活態度,一切都無所謂。

默爾索對生活的無所謂,還表現在不求上進上,老闆想提拔他,他拒絕了,理由也簡單:
我們從來不能改變生活,無論如何,生活都是一樣的,我在這兒的生活也不會令我不高興。
老闆聽了默爾索的話,只覺得掃興,或許更多的是不理解。
除了工作,在感情婚姻上,他也抱著無所謂的態度。
女友問他是否愿意跟她結婚?
默爾索說都行,如果女友要結婚,那就結婚。
女友又問他是否愛她?
他說這個問題毫無意義,但他心里知道,自己肯定不愛她。
女友又問:既然如此,那你為什麼要娶我?
默爾索說這無關緊要,她要結婚,他說一聲同意,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就算不是女友,而是另一個女人問他會不會跟她結婚,他也會說當然,默爾索的態度,讓女友傷心。
傷心之外,只覺得默爾索是個怪人。
後來,一個陽光明媚的周末,默爾索和雷蒙去海邊度假,碰見了雷蒙的仇人,默爾索被太陽曬得昏昏欲睡,眼睛還蒙上了一層水霧,讓他視線模糊,他看見對方拿著刀向他沖過來,在緊張和恍惚中,他稀里糊涂地開槍打死了對手,然后又對著尸體開了四槍。
默爾索被捕了,預審法官問他找律師沒有,他還奇怪「一定要找一個才行?」
他覺得自己的案子很簡單,但預審法官說:法律是另一回事。
最終,法院給默爾索指派了一名律師,這位律師矮矮胖胖,頭髮梳得整整齊齊,他告訴默爾索,案子很棘手,但如果默爾索信任他,他還是有勝訴的把握的。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默爾索「殺人」這個事實首先被放在了一邊,法官和律師卻把目光投向了默爾索的生活。
首先被了解到的就是,他在母親的葬禮上無動于衷,表現得冷血麻木。
律師問他,是否可以說是努力控制了悲痛的心情?
默爾索說:「不,因為這是假話。」
律師又說,養老院的人將會出來作證,默爾索覺得,葬禮上發生的事與案子毫無關系。
律師很生氣。
法官又將默爾索生活的某些事情找出來,找到了別人對默爾索的看法:一個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人,他想知道默爾索對此有何看法。
默爾索說:「這是因為我從來沒有什麼值得一說的,于是我就不說。」
法官問默爾索,到底愛不愛媽媽?
默爾索說:「愛,跟常人一樣愛。」
「為什麼在第一槍之后,停了一會兒才開第二槍?」「為什麼還向一個死人身上開槍?」「究竟是為什麼?」
法官覺得,一切都很明白,只有這一點不清楚。
但默爾索覺得,這無關緊要,在此事上鉆牛角尖毫無道理。
法官問他,是否對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默爾索說:「與其說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說是感到厭煩。」
在監獄里的最初幾天,默爾索感覺不像是在坐牢,而是在等著某個新的開始,時間一久,他也習慣了,覺得這樣的生活也是可以忍受的。
審訊一次次地進行,默爾索在別人眼里也越來越奇怪,最后,默爾索對生活的態度,甚至決定了案件的結果。
對母親的死,他沒有悲痛。
對結不結婚,他無所謂。
對升職加薪,他也沒關系。
一個對母親的死「無動于衷」、「麻木冷血」的人,殺人似乎也就理所當然。
"可以說,人們是在把我完全撇開的情況下處理這樁案子,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沒有我參與的情況下進行的,我的命運由他們決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見。"
默爾索被判處死刑。
行刑前的某個夜晚,夜空深邃,充滿星光,默爾索想到了母親:
如此地接近死亡,母親一定感受到了解脫。
任何人,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哭她。
在這個夜晚:
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融洽,覺得自己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為了善始善終,為了功德圓滿,為了不感到自己屬于另類,我期待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
在審判的時候,審判者一直在研究默爾索的生活:
他說他一直在研究我的靈魂,結果發現其中空虛無物。他說我實際上沒有靈魂,沒有絲毫人性,沒有任何一條在人類靈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則,所有這些都與我格格不入。
加繆說:
「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這是人們可以明確說出的表述。但是,荒誕是這一不合理性與人的心靈深處所呼喚的對理性的強烈要求的對立。」
世界本身才不管荒誕不荒誕,世界只是存在,并不管人的理想和價值、希望及意義。荒誕的是人對世界的期望和世界本身不會按照這種方式存在的對立。

文章未完,點擊下一頁繼續